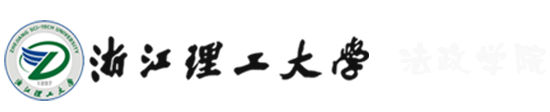目前,中国网民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0个亿。一方面,我们享受着互联网给带来的便利和好处;但另一方面,我们的个人信息也随着手机飘散到了四面八方。如果个人信息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,手机就变成了“手雷”——随时会“爆炸”,给我们带来危险。11月1日,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开始实施,在过度收集个人信息、滥用人脸识别、大数据“杀熟”、个人敏感信息等方面,法律都开始有了明文保护与制约。但是有了法,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从此就能走在安全的大路上了吗?有了法,又怎样才能更好的落地?
高钰涛,我校法学专业学生。她对人脸识别应用极为警惕,多次提醒同学若非必要,少用人脸信息。有一次,她偶然得知,消费者只要进入某商场,就会自动被抓拍人脸并注册会员,她便对此展开了调研。
她提到, “那边的工作人员对这种人脸识别,都不是很清楚。我们就去看那些摄像头,但是有些摄像头高,然后又看不清楚。就不能确定它到底是内部用的,还是说连接了一些人脸识别的系统。现在我没有办法去判断,我是不是里面的会员,当时它那个系统的披露,是说可以自动成为里面的会员。”
经过对AI社区的检索,高钰涛发现,2018年,该商场就利用某互联网平台研发的人脸识别技术,实现“入场即会员”,即为新顾客开通无短信通知的虚拟会员。她认为,新会员造访次数增加后,就会被认定为精准营销对象;而老会员被识别后,其在系统中的客户忠实度就会提高。该商场以此将顾客分为散客、常客、忠实顾客。
高钰涛认为商场严重损害了其个人与公众的合法权益,便向法院提起诉讼,法院于10月29日正式受理。而高钰涛在郭兵的建议下第二次进入商场,特意摘下口罩,以便正式取证。
郭兵补充道:“因为这些证据其实学生取不到的,只有互联网平台自己在网络平台上面公开披露整个过程,那我们消费者才知道。而且这也是作为学生这次起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。我了解到,这个证据现在已经被删除了。”
郭兵,浙江理工大学特聘副教授,注重学生法律知识的实践性。曾把收集他的人脸信息作为入园条件的某动物园告上法庭,被称为全国“人脸识别第一案”。
郭兵指出:“有一些它仅仅就只收集你的人脸信息。比方说,它没有你的姓名,没有你的手机号,也没有你的身份证号,这种风险相对小一些。但是这种风险小,并不意味着它没有风险 。因为比方说精准营销的这种场景下,它知道你天天去这个店,知道你喜欢什么品牌,掌握了你的行踪之后,它再进一步收集你的信息。这个时候,如果其它的商家,掌握了你的其它个人信息,然后你又有无感知的人脸信息的时候,它可以很容易通过一些认证的场景。这种时候违法犯罪的分子,他拿去干什么你就不知道了。”
他感慨道,对于商场对顾客人脸信息的侵犯,凭借常规手段难以举证。而现在的立法包括司法解释,确定了一个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。不可能让所有的消费者去举证商家收集了他的人脸信息。所以法律上,也是回应了这样一个常理,即让个人信息处理者,也就是让商家来证明,其没有侵害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权。
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对无感知信息利用作出规定:即个体意愿居于首位,且应当取得个人单独同意,确立以告知—同意为核心的一系列规则;同时相对于倡导性法规,个保法对个人信息处理者设立专章法定义务,如对重要的互联网平台,要“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,接受社会监督”。
郭兵在最后提出:“个保法出台之前,为什么没有长出'牙齿'呢?是因为它没有一个严厉的法则 。我们以前虽然有网络安全法,往往是以警告为主,就是责令你改正为主。个保法是大幅度增加了违法的成本,我们最高的罚款甚至能达到你上一年度营业额的5%,这个比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处罚的力度都大。但是执法部门能不能够严格去落实这样的处罚,肯定我们还是需要后面继续观察。”
面对形形色色的个人信息泄露,郭兵希望公众不要只图方便不顾安全,必要时要维权。至于维权成本,他更多鼓励法学学生去诉讼,而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更适合公众,公益诉讼,向有关部门投诉等,将以更省时省力的方式成为维护自身权益的常规武器。
放任个人信息泄露,我们的人生将被永久保存成数据,存在于网络的某个角落,包括着行为举止、生活习惯。但很多人不是一成不变的,我们一生都在改变和成长。个人信息保护可以帮我们获得第二次机会,我们有权删除某些个人数据。这允许我们成长和成熟,而不会被过去的错误而束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