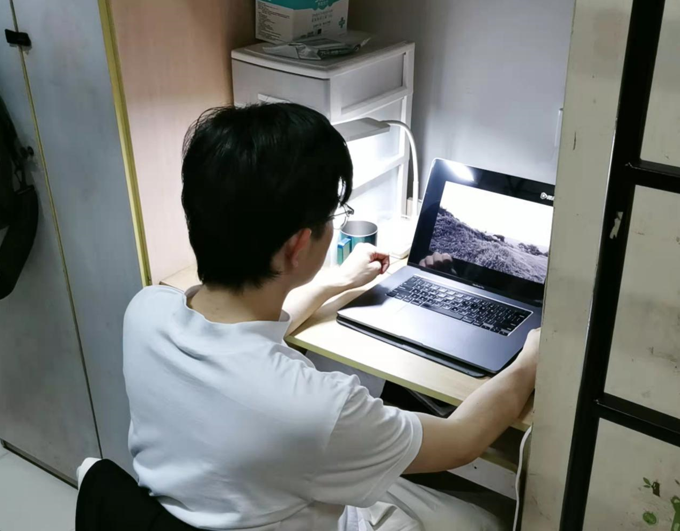三角形、梯形、正方形、螺旋曲线,数学家试图用最简单的线条解读世间万物。当远离书本、远离研究,这些几何图形也可能以别样的形式出现在一位数学教授的衣服上。他创建了中国微分几何学派,晚年创建开拓了计算几何新的研究方向。这位数学教授便是被称为“东方第一几何学家”的苏步青。
1902年9月,苏步青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的一个山村里,父亲靠种地为生,童年时代,“卧牛山下农家子”、“牛背讴歌带溪水”是他的日常。虽然家境清贫,但父母依然省吃俭用供他上学。刚开始学习的苏步青起先并不出类拔萃,反而因为贪玩,只考了班级倒数第一。但是在地理老师陈玉峰的谆谆教诲下,苏步青幡然醒悟,从此以勤为径、以苦作舟,学习成绩变为了全班第一名。
1914年,以优秀成绩考进旧四年制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学。中学时期,数学老师杨霁朝的一番肺腑之言“要救国,就要振兴科学;数学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,发展实业,必须学好数学”,确立了苏步青未来的一生信念,也将少年的他引入了数学王国,与之相伴一生。
1919年7月,年仅17岁的苏步青就在中学校长洪先生的资助下,远渡重洋到日本留学。十二年的潜心钻研,使他成为了微分几何学界的青年翘楚之一,有人称他为“东方国度上空升起的灿烂的数学明星”。
1931年初,学界的热情挽留,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,没有动摇苏步青的信念。为国家培养人才,怀着对祖国和故乡的深深怀念,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,苏步青终于回到阔别12年的故土,回到了积贫积弱的祖国。“我是祖国送出来学习的,学成后应该回去报效祖国”。到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,国内教学的条件很差,工资都发不出。纵使教育和科研条件匮乏,生活平淡艰苦,但苏步青甘之如饴,他拿起教鞭、尺笔,与他称之为良师益友的陈建功先生,共同致力于办成世界第一流的数学系。
可惜,1937年8月,随着抗日战争局势的恶化,方兴未艾的事业被战争无情地打断。天色昏昏,国难当头,日军的炮火正一步步逼近杭州。为了保存国家研究的珍贵资料,保留全体师生这一宝贵资源,苏步青和其他老师校务们一样,跟学生们一起肩挑手提,负载着沉重的书箱和行李跋山涉水,开始了西迁之行。穷困、饥饿和疾病袭扰着西迁途中的每一个人,而日军飞机的轰炸时时威胁着这群西迁文军的生命。
一日途中,日军空袭警报突然响起,飞机声隆隆轰鸣,苏步青和他的四名学生匆忙躲进了旁边一个狭小的山洞里。喘息方定,苏步青认真地说:“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数学研究室。山洞虽小,但数学的天地是广阔的。大家要按照确定的研究方向读书、报告、讨论。”后来的数学所,如今的数学与科学学院自此诞生,那四名学生今后也成为了数学界的精英人才。
后来,苏步青终于在贵州湄潭朝贺寺的一间破庙里安顿下来。写下了“平生最是难忘处,扬子湄潭浙水边”,以此纪念他在湄潭的时光。
停下了西迁的脚步,也告别了颠沛流离的逃难日子,可是苏步青的生活依然艰苦。由于战争,物价飞涨,加上家中人口众多,即使省吃俭用,身为浙大教授的苏步青,生活仍是捉襟见肘。他所穿的衣服也是缝了又缝、补了又补,补丁摞补丁。上课时,苏步青衣服的一个个破洞被学生们戏称为几何图形,当他转身在黑板上绘图时,学生们就悄悄议论起他背上的那些“三角形”、“梯形”来。
生活上的困难或许能吓退胆怯懦弱之人,而对于有意志、有毅力、充满信念的人,困难只是一种磨难,也是一层历练。那些几何图形不仅缝补了苏步青衣服上的破洞,表达了他对物质条件的淡泊态度,更坚定了他教书育人的信念,夯实了他科研兴国的决心。
抗日战争胜利后,校外的政治风雨在一步步侵蚀学院的净土。苏步青不喜欢介入这些事件,但是为了保护优秀学生这些科学救国兴国的火种,他毫不犹豫地成为了学校的训导长。训导长本是国民党专门设立、用以镇压学生运动的工具,但是苏步青不记个人得失,甚至不顾个人安危,在此头衔之下,掩护保护进步学生,直至解放。
为了给学生们写一本包含自己最新的几何研究成果的优秀教材,在不知多少个深夜里,苏步青就着一盏昏暗的桐油灯,埋首整理撰写文稿。正是这十年磨一剑的坚持,在湄潭破庙的香案上,他完成了那本让业内惊叹的《射影曲线概论》。
苏步青常说:“个人的成名成家是次要的,重要的是要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,努力使我国的科研教育事业不断发扬光大。”苏步青真正做到了矢志报国、为国育才,他的名字也必将在群星中闪耀,照亮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前行的道路。